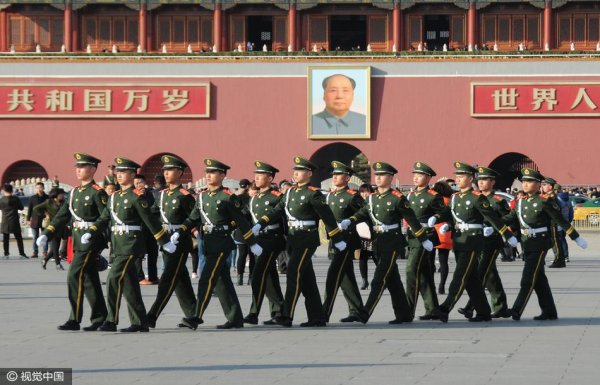2017年2月3日,央行将7天逆回购利率上调10个bp,由2.25%提高至2.35%。14天和28天逆回购利率同幅度提高。央行此举被市场普遍解读为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事实上,逆回购利率的微调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事后观察,当时逆回购利率的微调方向与紧随其后的货币政策走向也并不完全一致。
据此,此次逆回购利率的上调,到底意味着货币政策已回船转舵?抑或是央行寻求以更为灵活的手段,试图在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微妙平衡?
1、稳增长与防风险灵活进退的工具:逆回购利率变动的历史回顾
央行开始进行较为频繁的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是从2012年5月开始的。自2012年5月至今,7天逆回购利率共发生过22次变动,观察历史数据容易发现,2012年至今1年期贷款利率始终处于平稳或下行的状态,7天逆回购利率的大体走势虽与1年期贷款利率相近,但期间却出现过数次短暂的逆势上行。

具体来看,2012年以来,除本次(2017年2月3日)的逆回购利率上调外,7天逆回购利率此前还经历过4次上调,其中有3次在上调后不到1个月就又转而出现下调,其中更有2次则是在上调后不到1个月内便回落到上调前的水平。

细观历史,2012年以来的逆回购利率上调往往与防风险、去杠杆或防泡沫等有关。
对于我们图表2中归纳的第一次、第二次上调来说,直接的触发因素是“稳增长”无虞的情况下,2012年6月社会融资规模放量,达到近1.8万亿。同时,非信贷融资也迅速增加。比如,2012年上半年,信托资产余额同比增速达到48%。上述情况直接促使央行在2012年7月和8月两次提高逆回购利率。


对于第三次、第四次上调来说,也与2012年极为相似,在2013年的两次逆回购利率上调之前,都出现了社会融资规模放量,2013年1月和3月出现了超过2.5万亿的巨额社融。而同业加杠杆现象快速蔓延,2012年至2013年6月,其他存款性公司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的平均同比增速分别高达35%和34%。同业的扩张诱发国内当时关于影子银行的讨论和担心也几乎到达了白热化,作为一个外部可以观测的表征,则是最终在2013年末,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治理影子银行的“国办107号文”(即《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政策实际运作中的经验,往往在中央或国务院的文件正式公开之前,相关政策部门就已提前采取行动;在政策公开之后,相关政策行动往往已进入半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每一次的“防风险”行动,都是在经济增长暂时无虞的情况下方才切实展开的。2012年的第一和第二次逆回购利率上调前夕,工业增加值同比相对平稳,CPI同比回落至2%左右。2013年的第三和第四次上调前夕,工业增加值同比明显改善,通胀水平虽小幅反弹至2.5%以上,但仍然温和可控。没有明显稳增长压力的环境,赋予了当时的货币当局相对宽裕的操作空间。在全部四次上调发生之后,随着其后工业增加值相对前期出现放缓,逆回购利率旋即由此前上调转为下调。
与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往往在短期内具有极强的刚性相比,逆回购利率直接影响银行间流动性,且方向转换更为灵活,使货币当局能够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进退自如。

2、稳增长与去杠杆的平衡:当前之情势
面对1月例行高信贷,必须有效引导预期。从最近几年的历史来看,每年1月份均是1年里新增信贷量最大的月份;更为重要的是,自2013年以来,下一年1月份的新增贷款量都必然会超过上年同期(参见图表7)。1月新增信贷“量最大”和“超上年”的两大特征,不能说完全没有其现实的合情合理之处,但其也的确可能诱发市场预期偏离政策当局之所期。比如,伴随着2009年第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近4.6万亿的空前天量,此前一度下行的70大中城市房价上涨通道于2009年3月开启。几乎如出一辙的是,在2016年1月贷款投放量超过2.5万亿,再度创下贷款单月投放空前之最的时候,各地房价也由此急剧升温。如果再创新高的情形在2017年继续重演,很可能令楼市“防泡沫”的工作更为被动。在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7年的工作时曾明确要求,“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在此背景下,除了必要窗口指导,央行显然必须得“公开”出手,以全市场都可见的实际行动,来有效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

既然必须出手,剩下的就是手段选择的问题了。从可以公然宣示、引导预期的手段来说,央行似乎有很多可以选择:上调逆回购和干脆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是,由于存、贷款基准目前仍然是绝大部分贷款定价基准,其上调将立刻提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包括大量的存量贷款融资成本);同时,存、贷款基利率的调整往具有极强刚性,一旦调整便很难在一年半载内即迅速逆转之先例(若经常出现此类情形,则会对政策当局在形势研判上的权威性构成不利影响)。正如我们前文所回顾的,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刚性不同,逆回购利率的上下调整更为灵活,其变动向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传导更为间接、所需时间更长,非常适合作为临时性的手段采用。实际上,从当前的宏观经济状态来看,目前经济企稳的基础仍不稳固,货币政策并不具备进行方向性调整的条件。尽管2016年第四季度GDP增速出现小幅反弹,但经济改善的可持续性仍然存疑。首先,2016年12月,PMI、固定资产投同比、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和工业增加值同比等几个标识经济增长的指标均同时高位由升转降。PMI方面,PMI自2016年8月起逐步提高。但2016年12月PMI由11月的51.7下降至51.4。固定资产投方面,2016年9月至11月,固定资产投增速呈现出小幅改善的迹象。但12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由11月的8.3%回落至8.1%。工业企利润方面,2016年7月起,工业企利润同比增速总体不断加快。然而,2016年12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却由11月的9.4%回落至8.5%。工业增加值方面,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也从11月的6.2%下降至6%。



其次,通胀水平持续抬升的可能性较小。从PPI来看,与PPI同比走势高度相关的南华综合指数同已经在2016年12月突破了历史高位,达到61.8%。2017年1月,南华综合指数同比出现回落下降至59.7%。由此来看,PPI同比进一步上涨的空间有限。从CPI来看,年度CPI同比的走势与CPI翘尾因素的走势基本一致。2017年CPI翘尾因素为0.62%,略低于2016年的0.65%。因此,2017年CPI同比涨幅相对温和可控。
综上,当前为引导信贷合理增长并降低金融杠杆,央行通过上调逆回购利率,当然是货币政策的临时边际性收紧;然而,在经济复苏基础不稳、通胀压力有限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尚不具备掉头转向的基础。“稳健中性”仍将是未来一个季度货币政策的主旋律。随着前期去杠杆、去泡沫行为的持续,泡沫的风险会逐渐下降,而稳增长的重要性则可能再度上升,由此将令未来政策重心再度发生转换。(作者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兴业研究副总裁、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曾静